【拆廠紀實】農地工廠的試煉之路(完整版)
您在這裡
您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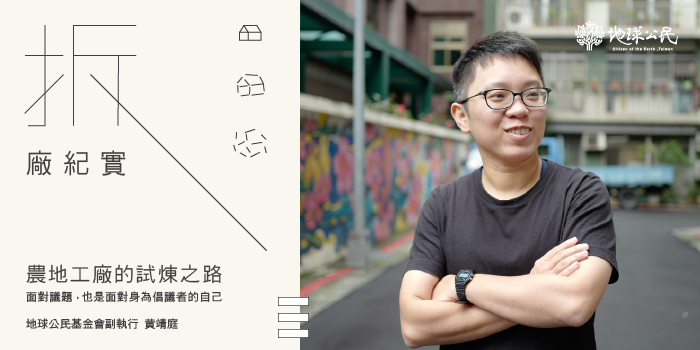
▌面對結構
倡議過程最困難的,是找到正確施力點。在違章議題上,我們讓政府建立跨部會合作與查處機制,從消極轉向積極。
違章工廠是長在農地上的違法建築統稱,實際上有很多樣態,造成的問題也很多元。最容易遭人詬病的,是有在營運的工廠。它們多半會有噪音、污水排放、氣味等外顯的環境問題。倘若只是一個鐵皮建物尚未成為工廠,通常作為倉儲使用,則會有景觀、遮陰影響到鄰地作物生長的問題。
這些在農地上突兀的鐵皮建物,在西部平原多如牛毛。在 2019 年《工廠管理輔導法》(簡稱工輔法)修惡的情境下,新增建如雨後春筍不斷冒出無法遏止。即便中央和地方政府採用多元手段抑制,也無法降低新增建的增加速度。這讓身處重災區縣市的居民,認為違章工廠議題倡議並未發生實質效果,等同於無效。
地球公民從 2016 年開始關注違章工廠議題,促使農業部公告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及第一波拆除名單,最終在 2017 年成功拆除 3-4 間(數字待確定)。2018 年我們到日本參訪處理違章工廠的經驗並產出一份調查報告,2019 年參與《工輔法》的修法,確認要求特登工廠 20 年落日。2020年,我們促成立委定期召開跨部門的平台會議,針對違章工廠處理政策面進行四次對焦討論,讓經濟部中辦、農業部、國土署橫向協作,公開新增建資訊、中高污染的查處結果、低污染的那管進度等,也促成行政院食安辦成立跨部門合作的農地污染資訊平台。
一年一年不同的行動,會在不同關鍵點開花結果。制度上改革我們也著力不少,包括監督《工輔法》子法內容,將非屬低污染認定標準從 36 項調整為 51+2 項,讓輪胎製造、水泥製品製造、瀝青混凝土、鋼鐵鑄造業...等行業都列為中高污染,這些產業與農地不相容,需要離開農地。我們也促成農業部源頭斷水斷電、阻擋違章工廠紓困、300 坪以上違章廠方查處法規修正,只要大型違章都有法可罰、透過查處人力經費與預算盤點,促成查處 SOP 流程建置及增聘查處人力,各縣市政府查處違章工廠人力增加一倍(2022 年數據,未更新到 2023 年)、避免污染工廠申請納管合法化、要求改善消防及污水處理設備…等。
改變有在發生,只是違章工廠依然存在,甚至持續增加。
從數據上看,就會覺得議題倡議沒有成果、糟糕的事情沒有因為倡議變得比較好。但仔細觀察,公務機關對違章工廠的處理態度從燙手山芋到專案處理,甚至成為各縣市政府的重點執行工作。不同部會之間本來是互不聯繫各做各的,透過平台會議開始交流資訊、共商可行的做法,中央到地方也開始有直接溝通處理此題的管道和工作流程建立,立委質詢朗朗上口,雖然切入談論的角度不見得相同,但違章工廠的議題確實已經成為更多人認知到的亂象,這些都是數據所呈現不了的改變。
▌面對社會
倡議也不只是公民團體與政府的事,如何傳播和捲動公民參與相當重要。
另外還有兩個創舉,是違章議題獨有的。一個是 2019 年地球公民和 g0v 零時政府開源社群共同發起「農地違章工廠回報」系統(簡稱回報系統),另一個是 2022 年持續與開源貢獻者打造出「空拍圖比對計畫-大家來找廠」(簡稱大家來找廠),這兩個系統讓違章工廠成為更多民眾參與管道的環境議題。
回報系統服務著有檢舉需求的民眾,這些民眾通常與違章工廠有共同生活圈,並且受制於台灣鄉里以和為貴的氛圍,無法承擔吹哨者角色。但是有了回報系統的匿名功能,民眾舉報意願提升,成為維持土地秩序在各個村莊角落的公權力延伸。截至 2023 年 7 月底,回報系統進站人數達54830,回報案件數達 2,965 (+125),且此系統也在志工夥伴的努力下,進入中小學教材中。
大家來找廠則是採用聚眾一起玩遊戲的方式,核實農業部的農地資源盤查成果。這讓嚴肅的議題多了趣味和遊戲感,也讓公部門投資在衛星影像上的資源得以被有效利用。不僅是議題行銷的創舉,也讓新增建違章工廠的議題打開知名度。此遊戲於 2022 年 5 月上線,超過 7,000 人次上網參與,監察院還因此將新增建違章工廠列為重點觀察項目,要求經濟部列管追蹤,經濟部也因此密切觀察這些個案。
在面對公眾時,我們試著先讓大家「聽過」議題,接著就是「了解」議題。違章議題牽涉到的法規和部會非常多,倡議者往往會陷入「如何把事情講得清楚、好懂、又不會偏離事實、又可以抓住眼球」的困境。
例如在違章議題裡同樣是在農地蓋建築物,有「生產事實」的建築物叫做「工廠」,主管機關是中央的經濟部和地方政府中的經發單位,若「無生產事實」的建築物則叫做「倉儲」,主管機關就變成中央的內政部和地方的建管單位。以及因為是「農地」上的違規使用,因此也跟中央的農業部、地政司和地方的農業單位、地政單位有關連。寫到這邊,是不是已經可以感受到一個議題背後的複雜性了呢?
▌面對倡議
我們必須邊研究邊行動,面對議題背後實踐的困境,找到短期成效與長期可執行的平衡方案。
違章工廠議題橫跨了不同中央和地方的單位,整個要拆除、查處、輔導合法化等等的制度,也就非常的複雜,地球公民花費非常多力氣複雜梳理清楚,再從中找出可以監督、倡議的著力點。也因此,這個倡議主題到了後期,會進入非常瑣碎、難懂、不易傳播的環節。
舉例來說,當一個違章工廠發生了火災,造成進火場救災的消防員喪生,這時候以倡議面來說,就是一個適合談論違章工廠應該立即拆除的政治時機,很殘酷也很現實。但光是要釐清這個工廠建築物是哪個時期蓋起來的、什麼時候開始有水有電及生產事實、執法漏洞是出現在哪個環節、哪個單位瀆職、工廠內部的消防設備與防災措施是否有缺乏稽查或者沒有落實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都牽涉到超級多的法令、法規,相關的部門和可以有責任的公務員也逐繁不及備載。
一但開始追根究底時,我們就發現,當好不容易要求或逼迫中央單位把制度建置好後,地方政府的執行才是最大的困境。專業人力不足、地方利益盤根交錯,導致第一線的地方公務員必須面對沒有執法的責任風險,也要面對地方勢力的壓迫,民眾陳情、民代施壓、首長選票壓力等等,其實真的不是一時能改善的。
因此,拆除掉多少間違章工廠、農地上還剩多少違章工廠、新增建是不是有即報即拆...等數據,已經不是環境倡議團體追求的「倡議成果」,反而是很難一眼就看清的「制度面的建構」才是重點。因為身為一個小小的環境 NGO,確實沒有辦法把這複雜難解的歷史共業一肩扛上身。我們透過細緻研究,要求政府建構出清楚可以執行的制度,才是最適合的位置。最後剩下的就是等待第一線執法人員增加、民眾意識的提升、跨部會的協作機制成為常態運作等。
面對自己
做倡議久了會知道,真正的強大不是一人扛起一切,而是能與夥伴協作、在無聲中繼續堅持。
倡議者的心理素質,一直都是倡議工作的關鍵。
從倡議目標的設定開始,就必須不間斷的省思哪裡我們可以著力。有時一些非常細微的改變會非常耗力,例如:違章工廠到底有多少?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去爬梳經濟部的工廠登記、農業部的農地流失數據、內政部的衛星變異點資料。然後我們會發現這些政府資料常常沒有公開,就算有公開,每個單位啟動資料累積的年度也不相同,非常難以比對。
因此如何將複雜難解的資訊去蕪存菁,找出一個可以說清楚講明白的路徑,這件事本身就非常有意義。因為民眾參與的前提是有充足資訊、政府部門願意開始調整的前提,也是有被指出明確無法反駁的問題亟需改善。在這冗長、枯燥的資訊梳理過程,倡議者要能耐得住無聊,接受沒有掌聲,一頭鑽進艱難的轉譯工作。這些歷程其實非常需要有夥伴、團隊一起協作,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包辦所有事項,所以我們會與擅長處理數據、製作圖資、公共溝通、媒體經營等夥伴一起協作。因此,倡議者的心理特質上必須能團隊合作,知曉自己一個人是無法創造影響力的。
再者,當倡議目標很宏大時,倡議者通常會很沒成就感。因為往往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才有可能達成偉大的目標。我必須指出,遠大的目標可以是願景,但要能梳理出「可達成的階段目標」才是重點。因為宏大的願景是透過一點一滴小成果累積出來,絕對不是一觸可及。另外,要做制度面的改革,在台灣社會情境下,往往無法就事論事談論議題本身,會有許多政治因素牽涉其中。因此倡議者也需要有能力分辨出哪些事情是自己的責任,哪些事情其實不可控。當那些不可控的事情發生,導致倡議失敗時,並不需要對自己咎責。休息一下,保持信念,重新梳理運動目標,才是倡議者必須努力習得的能力。
在跟民眾對話時,如果倡議者願意說出多一點工作上遇到的困難、瓶頸,願意聽你講話的人就可以理解,其實倡議者跟所有人一樣,都是能力有限的人。喚起民眾的同理心、願意支持理念,並理解倡議是一種持續在困境中找方法前進的態度。這樣的社會改變或許比每個倡議具備輝煌戰果,更重要。這也是我認為倡議者真正的強大,不一定是促成巨大改變,而是可以帶領民眾看見問題的核心、擁抱通往美好願景的路徑。要達到這一點,倡議者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過於強調犧牲的人,往往演變成我執很強的個人主義,在當代有時反而不利於議題的推廣、理念的擴散。

